抑鬱的文學與宿命的盜匪
尚‧皮耶‧梅爾維爾
1917‧10‧20─1973‧8‧2
文/黃建業
法國新浪潮起浪揚波,至今已經半世紀。然而,每次重放這些經典之作,仍感到那反叛年代桀驁不馴的開發力,五十多年間,電影世代感性和趣味的更迭,在峰迴路轉中,全然又是另一片天地。金馬影展在今年選擇了新浪潮教父尚‧皮耶‧梅爾維爾作完整的致敬回顧展,真的有幾分逆潮流的獨見和勇氣!
尚‧皮耶‧梅爾維爾在大師巨匠的星河系譜上,確實是一個難以歸位的獨行俠。往上溯源,他跟三、四O年代的詩意寫實掛不上邊,與他同時代的法國影壇,也不易於接軌。我們儘管稱他為新浪潮教父,他自己卻努力與六O年代的新銳保持距離。或許,這正是五O年代法國某些重要創作者們的特別之處,舉凡羅伯布烈松(Robert Bresson)、賈克大地(Jacques Tati)、尚考克多(Jean Cocteau)等,每人都以其獨一無二的電影風格,享譽影壇。這些大師身影,宛如戰後瓦礫堆中重新閃耀的珍寶,為法國電影於灰暗的時代裡,再展光芒。

要談梅爾維爾,可以從二次世界大戰前開始。1937年10月,梅爾維爾才二十歲,即投身軍旅,在佔領期間,甚至後來到英國,一直支援著抗德行動,而這些經驗完全表現在梅爾維爾改編自喬瑟夫凱塞爾(Joseph Kessel)名作的【影子軍隊】裡。正如梅爾維爾在【影子軍隊】開場時,引用的那句話:「不快的記憶,仍欣然接受,因為那皆來自離我日漸遙遠的青春。」
對德抗戰的經歷,對梅爾維爾而言,不單只是一種英雄式的愛國行動,更重要的是,它在混亂翻騰的時代裡,讓人性中複雜的情感、愛恨、理想與現實、信賴和背叛,都掉入崩解的不確定性之中。對梅爾維爾來說,這個不快樂的年代,但也正巧是他黃金青春歲月中彌足珍貴的經驗,在《梅爾維爾論梅爾維爾》(Melville on Melville,Rui Nogueira)一書中,他多次談及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了這個世界,那些美好的人、電影和事物如何在戰火中消逝。
梅爾維爾作品中相當重要的核心命題,無疑正是上述,那種陰鬱灰暗的時代背景。瀰漫在戰後困頓保守氣氛下的不安定感,帶著悲觀宿命情調的存在主義精神,無論前期的文學改編創作,或延伸到後期更具代表性的盜匪電影,梅爾維爾的作品始終滲透著這樣獨特的時代味道。

要瞭解梅爾維爾,仍從他早年的文學改編電影開始較佳,長片處女作【沈默之海】(1947)、【神父李昂莫罕】(1961)及【恐怖的小孩】(1949),甚至梅爾維爾本人較不喜歡的非改編作品【當你閱讀此信】(1953),均表達了梅爾維爾早年文學性風格。眾所週知,梅爾維爾是一位文學愛好者,其中傑克倫敦(Jack London)、艾倫坡(Edgar Allan Poe)等小說家,對他的影響尤其深遠,而他在讀完偶像赫曼梅爾維爾(Herman Melville)的《白鯨記》後,更感動得將本名Jean-Pierre Grumbach改為尚‧皮耶‧梅爾維爾。
在梅爾維爾早期作品的文學性影片,【沈默之海】是典範案例,正如他自己所說,這個影片的特殊之處,正在於它的「反電影性」。所謂「反電影性」,即是指該素材場景空間的單調感和非行動性的內心描寫。【沈默之海】改編自Jean Bruller Vercors於德軍佔領年代發表的小說名作,作品中最重要對抗行動,就是沉默,但經過梅爾維爾精彩的處理,不單只揮發出小說中冷冽沉寂的張力,大量內心旁白的風格,讓全片流露深沉的文學感性。梅爾維爾就曾驕傲地說,布烈松曾在《電影筆記》中坦言自己後來發展的極簡風格,即受【沈默之海】的影響。事實上,如果我們將【神父李昂莫罕】跟布烈松的傑作【鄉村牧師日記】(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,1951)一起放映,兩片壓抑性風格的近似性,真的會令人驚歎!

如果說【沈默之海】是梅爾維爾文學化電影的原型,【神父李昂莫罕】、【當你閱讀此信】及更早的【恐怖的小孩】,正是梅爾維爾文學性作品面向的不同發展,它們雖擁有各自的特色,卻醞釀著共通的驚人壓迫性和複雜心理張力。【神父李昂莫罕】隱晦的情感,【當你閱讀此信】的宗教省悟題旨,及【恐怖的小孩】中劇場式的寫實和幻覺風格的變化,處處呈現出梅爾維爾前期電影的風格命題轉換。這種戰後嚴肅的現代藝術觀照,讓梅爾維爾即使沒拍出後來的盜匪電影,在法國影壇勢必仍會佔有一席之地。
正如楚浮在評論【恐怖的小孩】盛讚該片猶如兩位大師美妙的四手聯彈:「尚考克多最好的小說,成就梅爾維爾傑出的電影,就如同巴哈和韋瓦第相互輝映。」(The Films in My Life,François Truffaut)文學的養分絕對是梅爾維爾電影中深具內在意涵的重要因素,若然大部分影迷都只看到他的盜匪片,可能就不知道早在【當你閱讀此信】這部1953年的文藝片中,這位大師的電影裡便己出現美國車、夜總會式酒吧、風衣呢帽的印記,筆者常認為他的盜匪片,只過是文藝片更個性化的轉型。沉默而讓人猜不透的張力依然,差別在戲劇性的心靈活動,轉為黑幫世界更為冷峻的凶險世界。

「在盜匪片中,一個人是沒有什麼選擇的。他有特定的看法、特定的做法。盜匪本身就是宿命。事實上,梅爾維爾的電影表現出一種哲學,只有那種法國人,那種法國電影痴狂才有的夢想,一種類型電影的存在主義。」以上是Stephen Schiff在評【賭徒鮑伯】的時候,所作出精彩的論述,道出了梅爾維爾的電影,不尋常的法式浪漫宿命色彩和魅力。從【賭徒鮑伯】(1955)、【曼哈頓二人行】(1958)、 【線人】(1962)、【第二次呼吸】(1966)、【獨行殺手】(1967)及更後期的【紅圈】(1970)與【大黎明】(1972),甚至以盜匪片筆觸處理的抗德電影傑作【影子軍隊】,都呈現出梅爾維爾孤峭而純靜的浪漫悲觀色彩。
盜匪片對梅爾維爾來說,就像貴族般的騎士走向黑暗的末路,呢帽風衣、手套正是他們保持最後的高貴姿態。【獨行殺手】讓他極簡主義鎔鑄成的美麗、純淨風格,無疑是影史上最具強烈藝術性的盜匪經典,遠從馬丁史柯西斯、昆丁塔倫提諾,以至香港的吳宇森、林嶺東及杜琪峰等,都明顯受他影響,而在影史上,也確實為三O年代美國盜匪片,打開另一個優雅的歐洲新局。深愛美國文化的梅爾維爾,從文學養分吸收到更深刻的類型透視力,才能如此自信地在戰後法國影壇創造出一片天地,並下開新浪潮廣浩的波瀾。
或許就如【獨行殺手】的引言:「只有林中的猛虎,才能暸觧武士的孤獨。」梅爾維爾仍以其優雅的孤獨姿態,向半世紀後的影壇,投下其容輕視的碩大陰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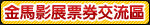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